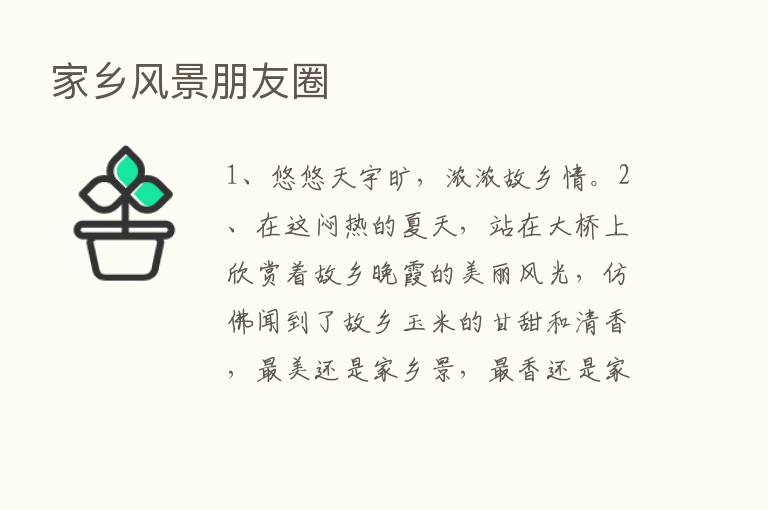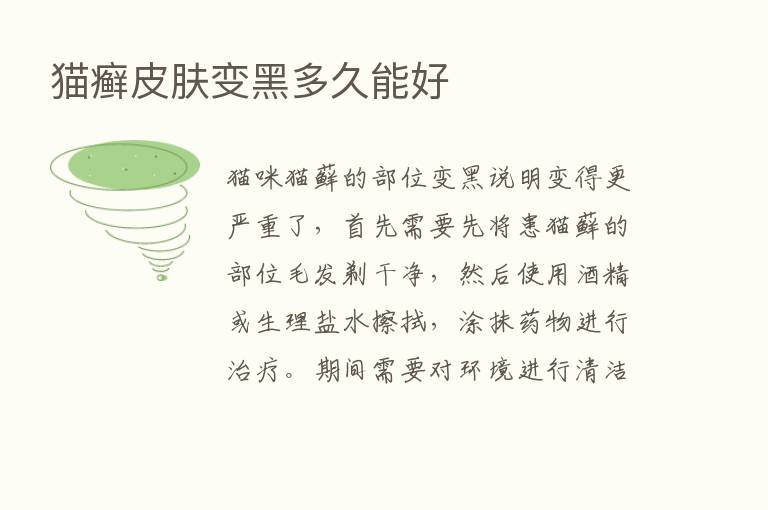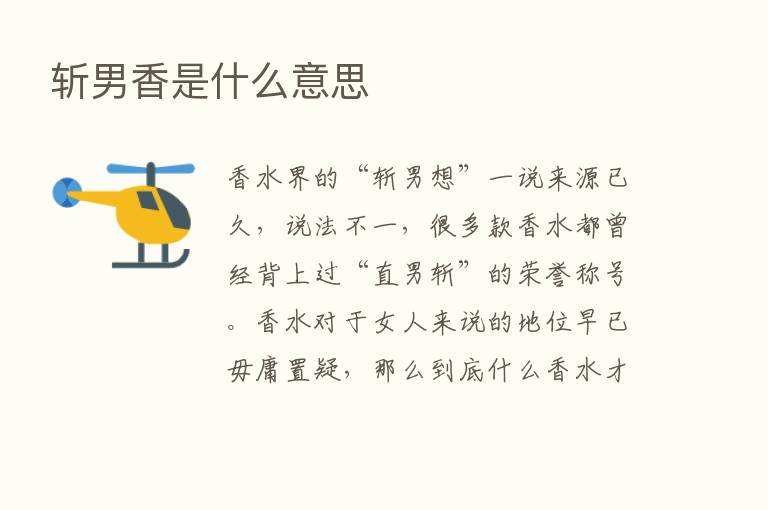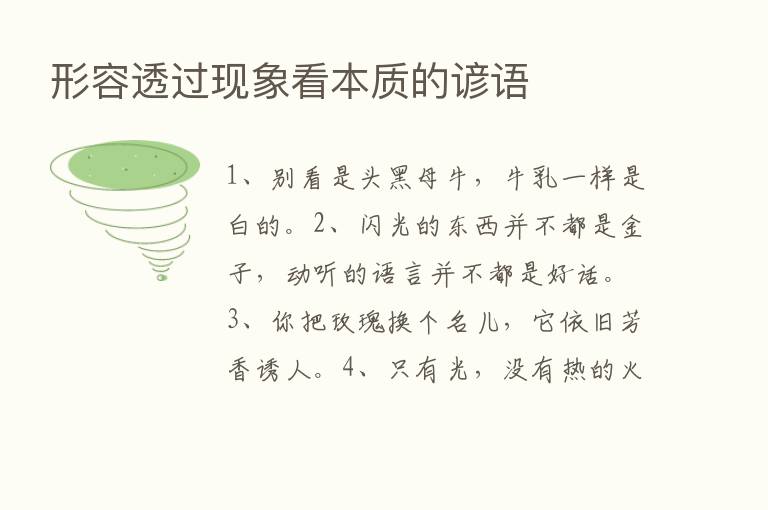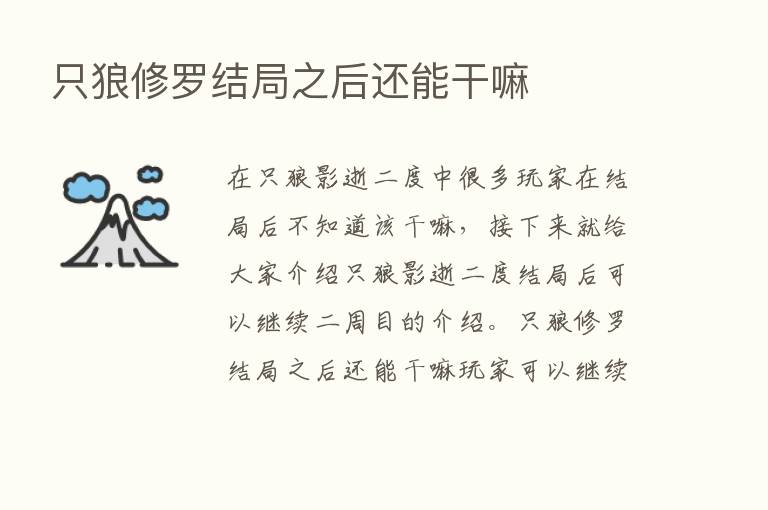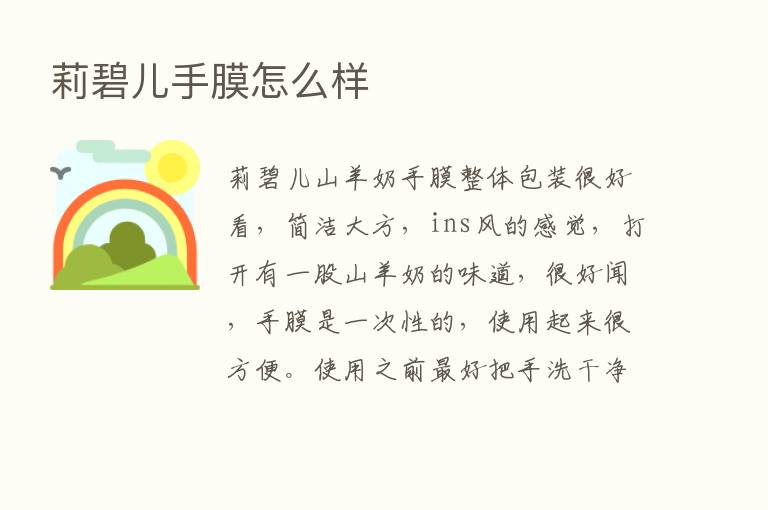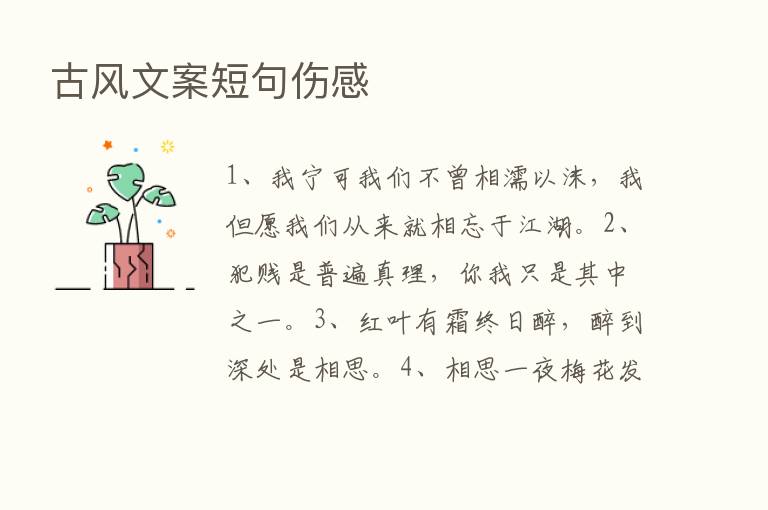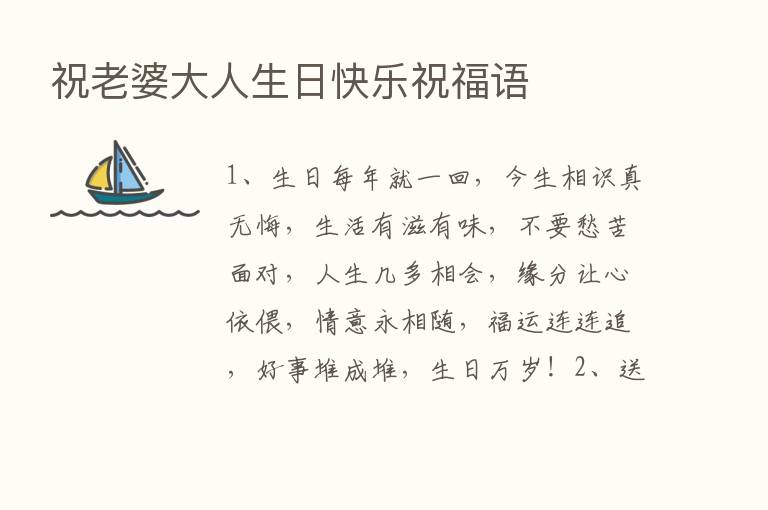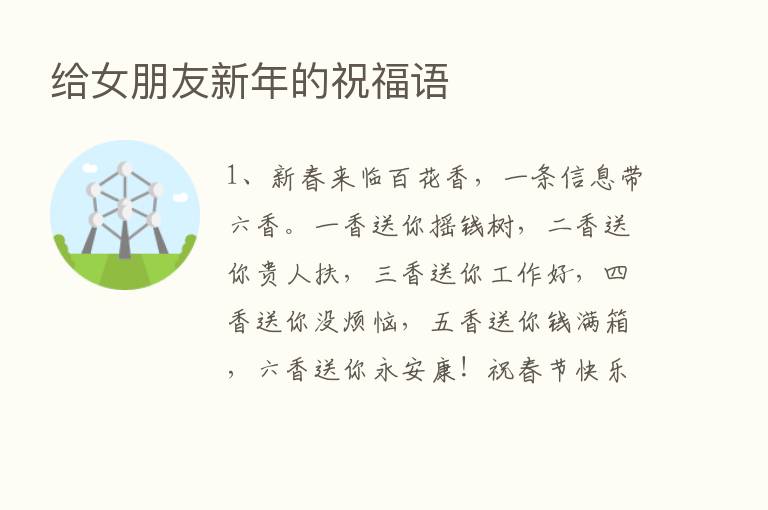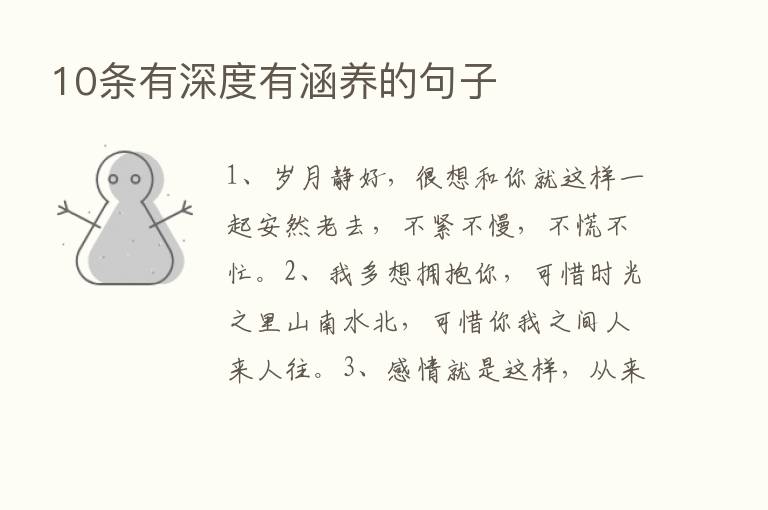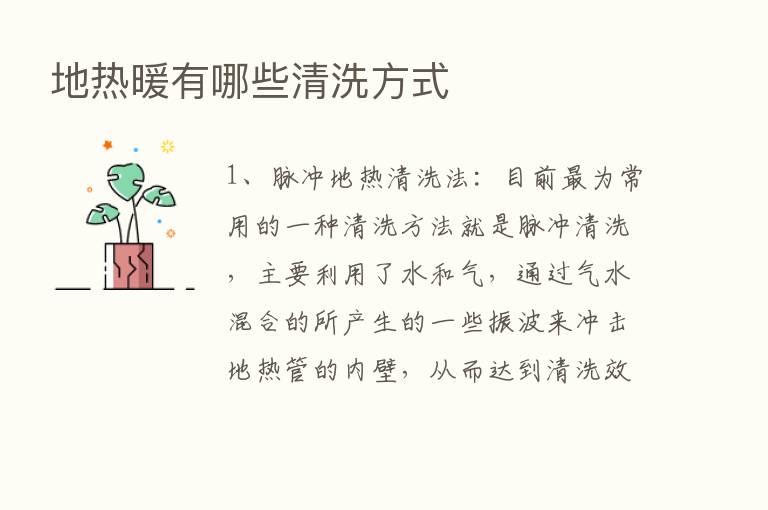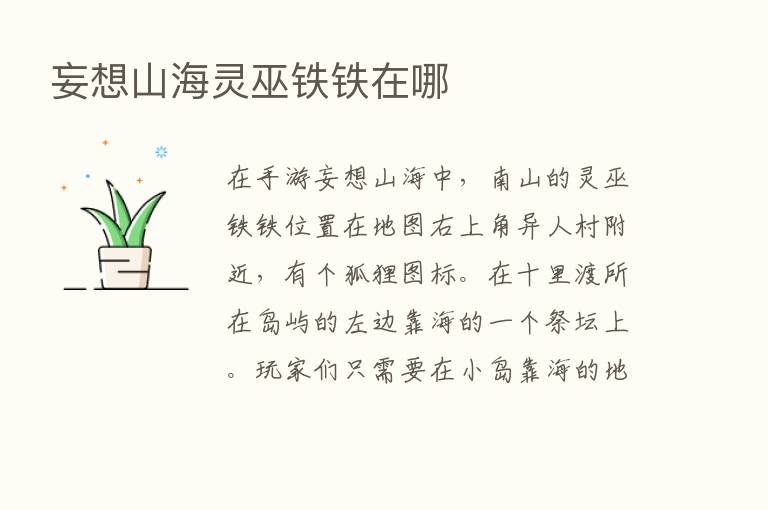潘素与张伯驹的爱情故事

江南才女潘素与北国公子张伯驹四目相对之时,已缘定终身,张伯驹填了一首《浣溪沙》:“隔院笙歌隔寺钟,画阑北畔影西东,断肠人语月明中。小别又逢金粟雨,旧欢却忆玉兰风,相思两地总相同。”以词表达心声,以才情打动少女的芳心。
张伯驹出生贵胄,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这样的贵公子早有妻妾,但潘素却不知。
当日后知道真相后,她已很难从张伯驹身边走开,只为情到深处无话说。
张伯驹曾称人生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
爱女人之说曾是风流倜傥的张公子所热衷的,他在娶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有媒妁之言的,也有自己娶回家的,然而张伯驹在认识潘素后,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他的心只系于潘素一个人身上。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
《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
张伯驹 一次见到潘素(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
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
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
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 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
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潘妃名花有主公子痴情“强夺”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 出了个张伯驹。
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
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
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
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潘素创作书画作品
“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这是张伯驹写给爱妻潘素的词,在张伯驹的世界中,与美和幸福有关的诗词,似乎都应该是写给潘素的。而这段来之不易的佳缘。让他们倍加珍惜。
婚后的生活才是二人幸福的开始,张伯驹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青绿山水。
毕竟有书香门 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潘素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
张大千、陈半丁、刘海粟、陶心如等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观赏珍藏,一起作画题字。
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画,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
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
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香凝夸奖潘素的画壮美、有气势。
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周恩来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
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
别人眼中的“败家丈夫”爱人眼中的“灵魂伴侣”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人世太多的兴衰罔替,潘素在温柔娴雅中透着独立自强之气。
在动荡的年代,为了让国宝不至于流失海外,张伯驹几乎倾尽所有,连家人都觉得他是“败家子”,可是潘素对他不离不弃,始终坚定地支持丈夫的一切决定。
上世纪30年代,潘素为支持丈夫购买恭亲王府的稀世珍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心爱的细软首饰,凑足4万银元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
后来,一位外商企图以30万银元的巨资购买,被潘素娩拒。而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是夫妻二人以110两黄金购得。
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了220两黄金,潘素叉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张伯驹一掷千金收藏文物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灾祸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绑架的对象就是张伯驹,一个汪精卫手下的师长放出话来,潘素如果不拿出300万赎金。休想救回张公子。
可实际上。张家当时已经拿不出那么多前财来消灾,大部分前已都购买字画了。
潘素昼夜难安,但是她知道,丈夫是绝不肯让她变卖国宝来求自保的。于是她变卖首饰,四处奔走,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以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之名也不胫而走。
潘素夫妻保护国宝
更为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使家中收藏的国宝免遭日寇掠劫,潘素将珍品缝在被褥和棉衣中,途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安全到达西安。
“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得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就大气也不敢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日后在回忆起这段惊险的日子时,潘素还心有余悸。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
但是就是这样拼着性命留下来的国宝,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并未拥为己有,而是从1956年起,将苦心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真迹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这阙作于1974年的《鹊桥仙》。是年近八甸的张伯驹写给相携40载的爱妻潘素的。
虽然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张伯驹和潘素却能“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一生相伴到老。
章诒和回忆潘素及张伯驹
上世纪50年代,章诒和(其父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部长等职务)曾向潘素学画,在她眼中。潘素的生活完全是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
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前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看似一则笑话,其实当时的张府已经捉襟见肘,潘素常常为了一家的生计而费尽心思。
1957年,张伯驹被定成“右派”,按照曾和张伯驹谈诗论作的陈毅元帅的指示,吉林省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亲自到北京请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 一副馆长(当时并无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教师。
1961年金秋,夫妇俩住进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的吉林艺专南湖宿舍。潘素不但常有力作问世,治学更是严谨,手把手地教学生作画。还经常拿来真迹给学生观赏。
1964年,伴随着中国登山队员登上希夏邦马峰的好消息,潘素的一幅浅绛山水《征服希夏邦马峰》问世,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被张伯驹的挚友们称赞为:“潘素是用登山队员攀登高峰的精神,在攀登青绿山水画的高峰。”
但是好景不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而潘素则要为北京市国画工厂画书签,两人靠亲戚朋友接济勉强度日。
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潘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伯驹曾被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但就是这样,在章伯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在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
“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章诒和感慨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而张伯驹与潘素坚守的恰恰是人生中 重情重义的坦荡胸怀。
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
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没能磨灭掉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
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潘素 爱的是张伯驹为她的画作《素心兰》填的词:“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1967年之后,张伯驹这个曾经的贵气公子变成了落魄老叟,潘素却仍然不离不弃,通过替人画书签赚前养家。
1975年,在张伯驹年近耄耋,与爱妻潘素小别,到定居西安的女儿家里暂住,即便是短暂的分别,他对她还是情深款款,写了首《鹊桥仙》给她: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时候他们的婚姻已将近四十年,却仍相濡以沫,爱意不减当年。七年后,他去世。再过十年,她也随之而去。
作为一个站在张伯驹身后的女性,潘素是幸运的,张伯驹也是幸运的。
如果没有遇上张伯驹,就没有她出色的艺术成就;如果没有潘素的出现,他就不会有那么完美和谐的家庭生活。他们是生活上的伴侣、精神上的知音,也是佳偶天成的范例。
推荐阅读:
潘素生平简介
民国十大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