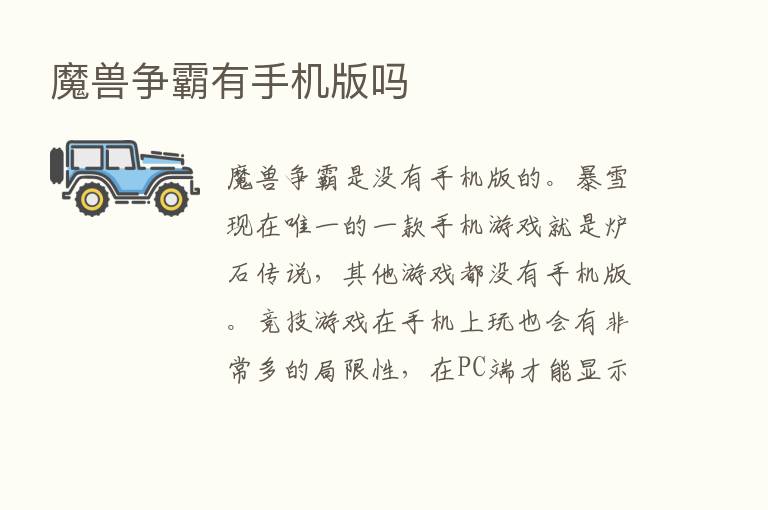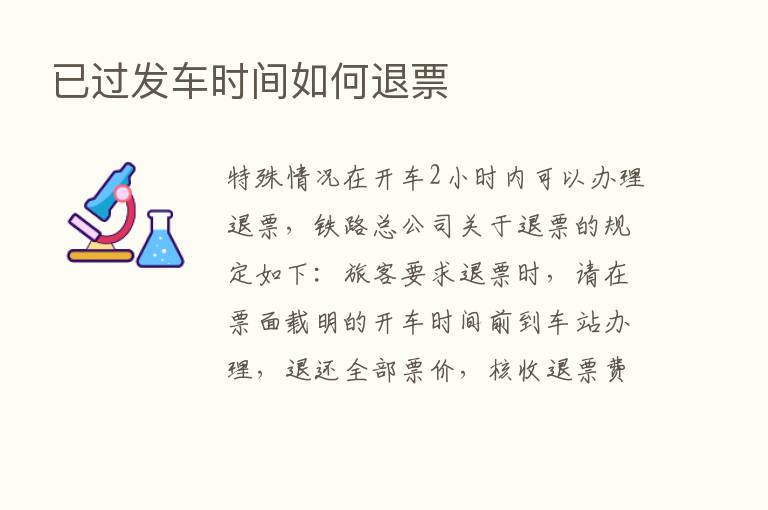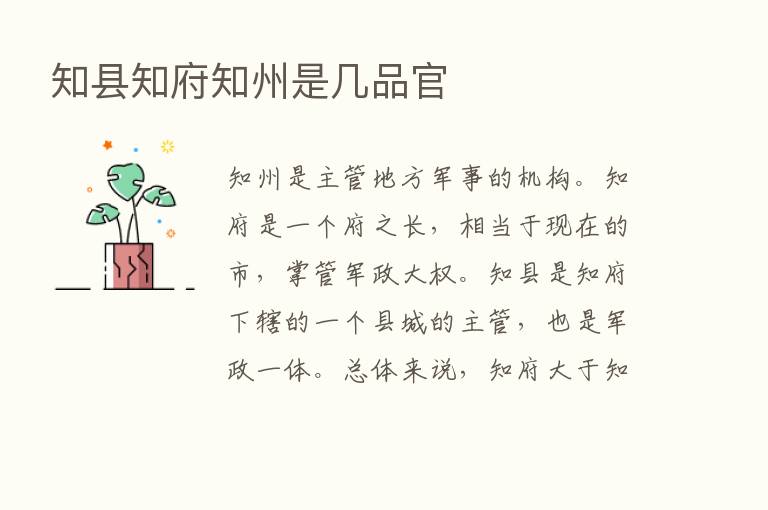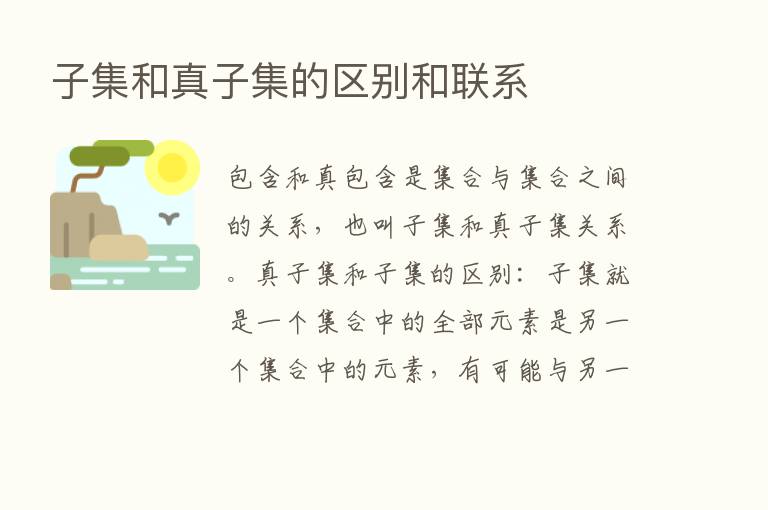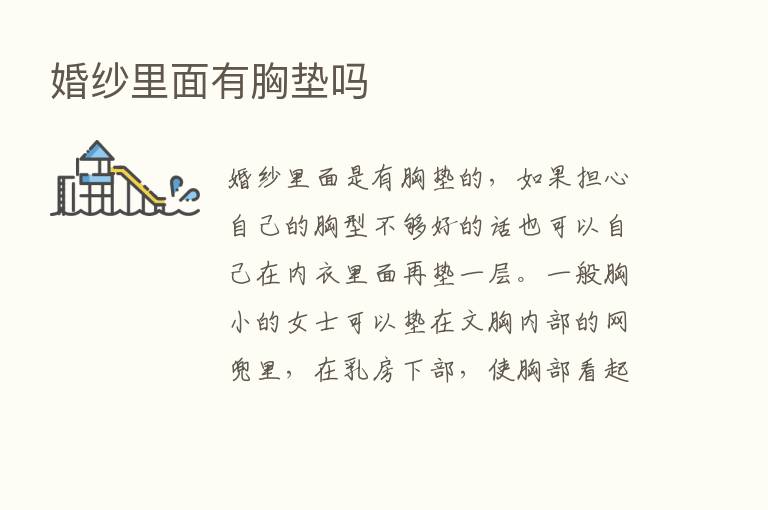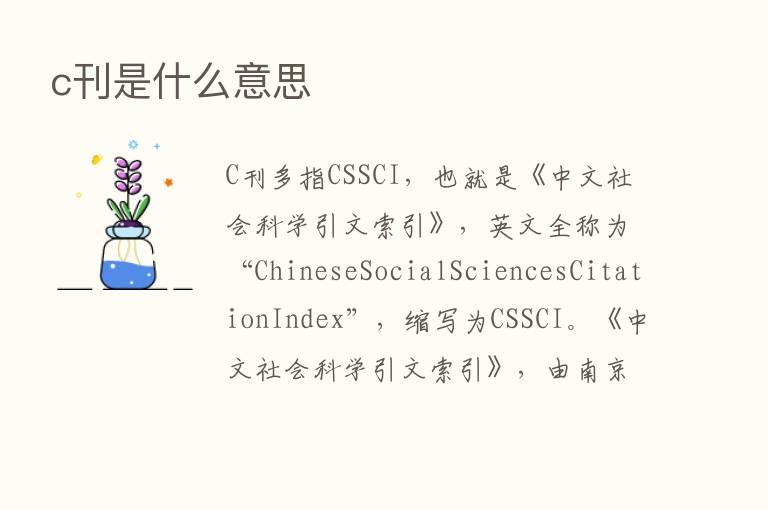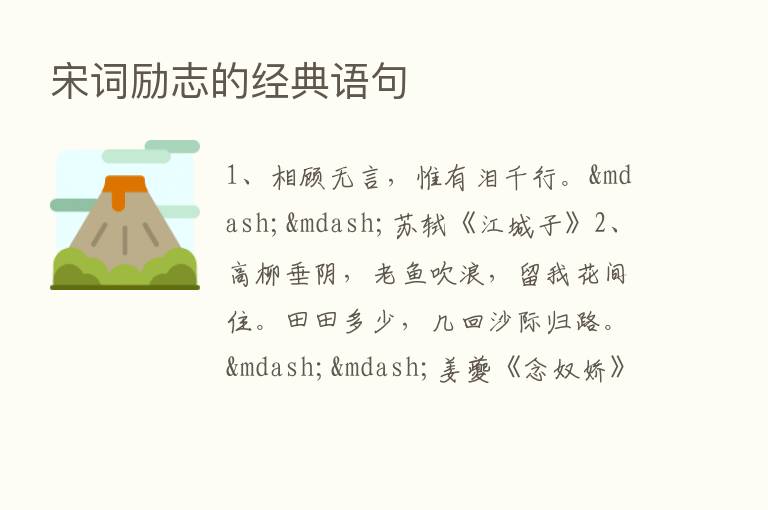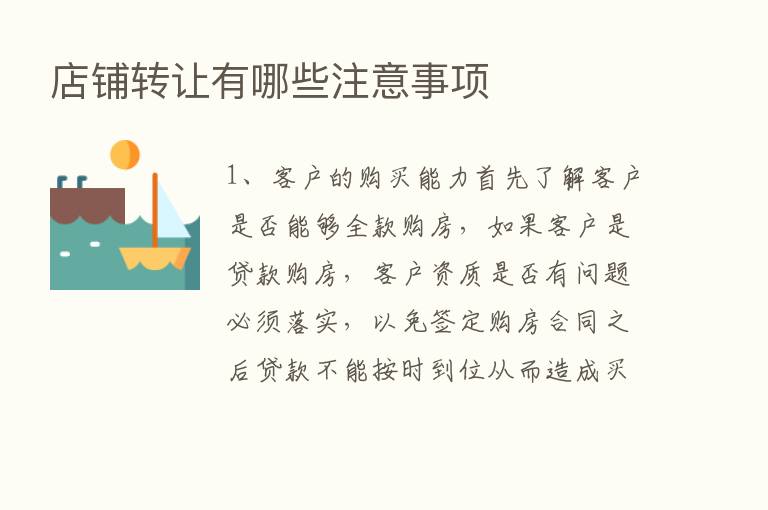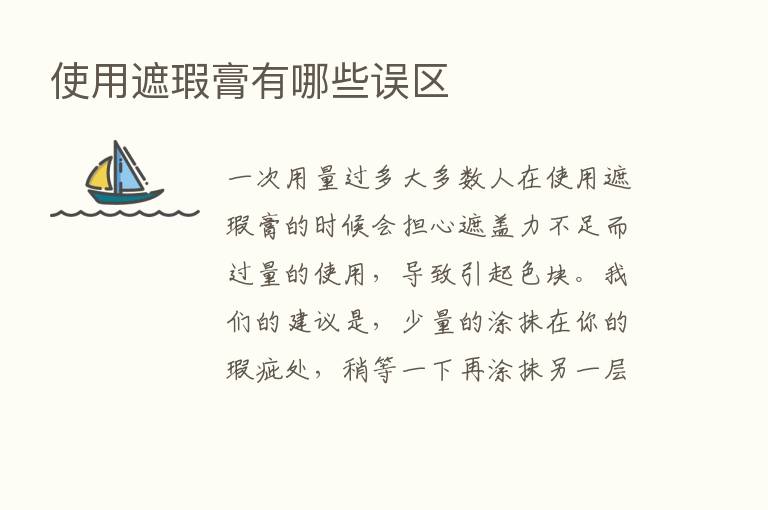土司制度什么时候开始的 播州杨氏势力是如何壮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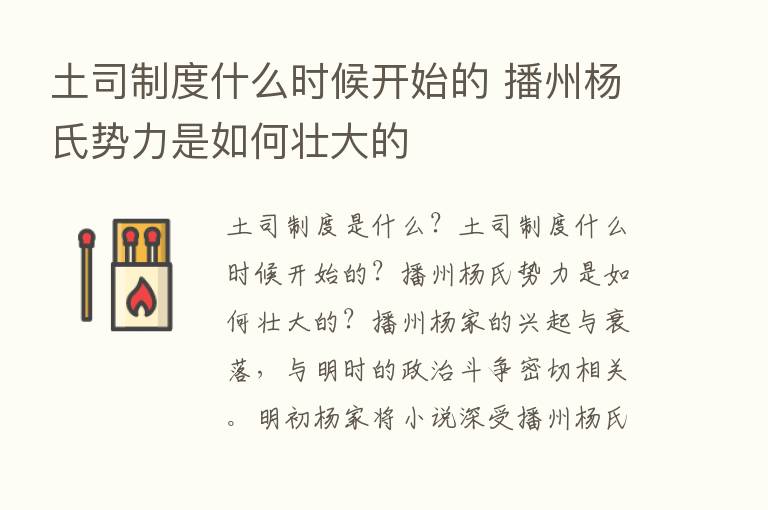
土司制度是什么?土司制度什么时候开始的?播州杨氏势力是如何壮大的?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 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神宗平定杨应龙(1551-1600年)反叛,把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从876年杨端统治播州,到1600年杨应龙被灭,杨氏统治播州历经29世,724年,成为贵州土司中势力 强的一支。
在这700多年间,中原及四川地区历经五代十六国之乱、金人之乱、蒙人铁骑统治、元末大乱,播州之境岿然,巴蜀流民多有归附。播州杨氏保疆垦土,屡有战功。这样一个家族为什么突然消亡了呢?这跟明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切相关。
土司制度始于唐,盛于明,播州杨氏土司在明时也盛极一时。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取道播州,准备平灭元军在四川的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元军,他派使者前去劝降播州杨氏。播州土司杨铿审时度势,率领大小官员来归。朱元璋非常高兴,对播州杨氏大加赏赐,让杨铿仍旧领命播州,部下大小官员任命等事务一切照旧,政府不向播州征收赋税。
1374年,中书省提议向播州征取贡赋以作军储,标准是每年纳粮2500石(一石约为120斤)。朱元璋否决了这一提议。他指出,播州杨氏在各少数民族中,是 早率众附归的,于朝廷统一有功,所以决定免掉他们的赋税,任其自由支配。由此,播州杨氏正式获得了包括税赋豁免在内的很大特权,他们只是每三年象征性地向朝廷纳贡一次。
在朝廷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播州杨氏的势力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们又得到了一份 ,播州杨氏的子弟可以入朝进入太学,由国子监官亲自督导学习。嘉靖元年(1522年),应播州土司的要求,朝廷赐给他们儒学典籍《四书集注》。
杨氏土司在自治的过程中,兵力不断壮大,多次帮助朝廷平定苗民叛乱和附近少数民族叛乱。到了杨应龙时代,播州杨氏已是湘、贵、川一带的名门望族,势力达到顶峰,屡屡与周边的土司、地方官以及朝廷命官发生冲突,贵州流官不满土官横行无忌、不服流官管束的霸道作风,矛盾已很难调和,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明史对杨应龙的描述基本都是反面的,说他好猜疑,性情残忍。1571年,杨应龙继承父亲杨烈之位,一开始表现得尚属低调,对朝廷毕恭毕敬,也屡受皇恩。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宫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因雷击起火被焚,杨应龙及时献上当地“大木七十”,因其“材美”,讨得朝廷的欢心,赐其“飞鱼服”,授予都指挥使一衔。
为了独霸一方,杨应龙对内酷 树威,不仅镇压播州一带的苗民,还屡屡侵犯四川汉人境地,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切。播州附近的一些土司也对他心存不满,朝廷中更是有人想要除掉他。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朝廷指出,杨应龙有诸多凶恶之事,巡按陈效则直接给出了杨应龙的24条罪状。但是在如何评价和处置杨应龙一事上,明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在黔的官员认为杨应龙罪大恶极,但蜀地官员认为其无可勘之罪,黔官便指责蜀官有意包庇。当时为防御松潘,播州土兵被征调协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潘地处险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巡按李化龙提议,暂免对杨应龙的勘问,准允他戴罪立功。
两派意见相左,明政府犹疑不决。其实,叶梦熊弹奏杨应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要推行所谓的“改土为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欲把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全部划归重庆管理。所谓“改土为流”,就是废除世袭土官制度,改为非本地的流动官员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播州杨氏对当地的统治即将化为乌有,杨应龙当然不会答应,所以极力加强对所辖五司的控制。
此时杨应龙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杨氏家族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朝廷的反杨势力抓住了把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杨应龙的宠妾田雌凤为了争夺嫡系之位 了嫡妻张氏。张氏的叔父张时照与部下何恩、宋世臣等人含恨上书朝廷,诬告杨应龙谋反。叶梦熊闻讯大喜,立即请求发兵剿灭杨应龙,但受到蜀地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蜀地三面邻播,与播州关系密切,而且播州兵将骁勇,多次受朝廷征调,立有战功,突然发兵征讨不是良策,应以安抚为宜。但是,谋反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朝廷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令四川、贵州两省联合勘调此事。杨应龙表态,愿意配合调查。不过他提出,黔地官员一向必欲除己而后快,所以他愿意赴蜀而不赴黔。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在重庆受审,结果被判定有罪,依法当斩。杨应龙大惊,急忙疏通各种关系以求活命,允诺愿以二万金赎命,正在狱审犹疑不定之际,国际国内突然发生的一场重大事变,使杨应龙逃过一劫。那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王朝决定发兵援朝,于是广征天下之兵。杨应龙闻讯,立即表态愿率五千播州兵征倭自赎。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杨应龙的所谓率兵援朝看来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回到播州后一直按兵不出,没有履行出征朝鲜的诺言。巡抚王继光前去督办,杨应龙仍然没有回应。此时,张时照等人再次上书弹劾,王继光遂发兵征讨。
征讨杨应龙的战事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播州辖内山高林密,道路难行,大明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差,在与杨应龙的交战中屡屡受挫。朝廷一时拿杨应龙没有办法,又考虑到东西两线同时用兵,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再次招抚杨应龙。
杨应龙借机上书表白,自己本不想叛乱,无奈受奸人陷害,事至于此,实非本意。 终,双方达成妥协,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羁押重庆以做人质,可叹的是,杨可栋在重庆被害。这件事对杨应龙的打击很大,他痛心之极,随后又反,散金厚抚诸苗,决心死战。
讨伐杨应龙的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历经8个年头,集8省(当时只有13个省)20余万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才彻底剿灭了杨应龙。讨伐杨应龙与平定哱拜、援朝抗倭被史学界称为 “万历三大征”,也是中国历史上 重要的100次战争之一,对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平播胜利意味着播州土司的解体,这是朝廷的意志,也是地方行省不断壮大的需要,更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必然的结果。
战后播州被一分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完全满足了流官们的愿望。播州杨家将既是四川、贵州两省利益分割争斗中的牺牲者,也是外来势力急于吞噬、抢占土著资源的政治牺牲品。到这个时候,明代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播州杨氏家族随着播州行政制度的改土归流而没落,“杨家将”说唱曲艺、讲史小说随之又发生了一场裂变。
平播之战结束之后不过两年,一部6卷本100回的说唱小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应运而生,其紧跟形势之快,令人咋舌,播州杨家将的基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北宋志传》的首刻本出现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朝廷决定对播州用兵的那一年,小说被删改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杨家府演义》则是在播州平叛结束之后出版的。《征播奏捷传》的快速出笼与杨家将小说的集中出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书坊此前印行的带有褒扬播州杨氏内容的小说,因为播州事发,在政府的干预下,不得不紧急改版重刻。
播州杨家将既已成为朝廷的反臣,那些为其歌功颂德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当然就不再合于时宜,当然要受到朝廷的清剿。没有人敢私藏,或者尽管有胆大包天者,但历经岁月沧桑,无法传得更为久远,所以今天再也见不到了。
杨文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 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 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 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 后 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 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 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书。只因该书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 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了解了这段历史,也许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之前的杨家府小说消失得那么迅速而彻底。在那种专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毁灭殆尽,因收藏书籍而被 的事件屡见不鲜。在播州杨氏事发之后,如果有谁胆敢收藏为其歌功颂德的作品,轻则肢体受损,重则性命不保,在这样的肃 之下,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话又说回来,其实朱元璋不是不喜欢戏剧,也不是不懂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个专家。“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朱元璋曾经有首诗:“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他的诗很显然是受了元人杂剧楔子引白的影响:“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 为关注的是,戏剧不能亵渎帝王皇权,他的这个禁忌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有许多例子可以作证。翰林编修高启做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御史张尚礼做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将全寺僧人尽皆 了。
明代的文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 同样有名。他们不仅 功臣、 贪官还 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 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 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 ,《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 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 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 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明代还专门设有锦衣卫,用以监视官员与百姓,厂卫特务横行,布满全国各地,动辄指人为奸,忠良官吏无辜受冤者甚多。人们时刻生活在心惊胆颤之中,当时官员每次入朝都要与家人诀别,到了晚上平安回来则以掌相庆又多活了一天。
在明代,从朱元璋始,巩固政权成了皇帝关心的头等大事,民族矛盾反而下降到次要地位。文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 ,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